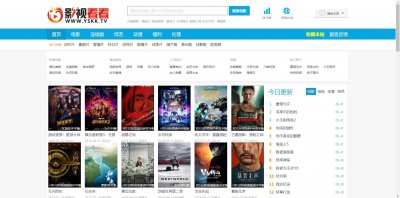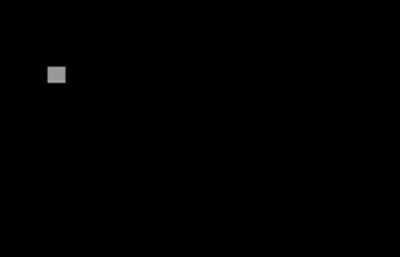《酒后》:“五四”时期女性作家对群体欲望与爱情伦理的书写
《酒后》:“五四”时期女性作家对群体欲望与爱情伦理的书写
在文坛大家辈出的“五四”时期,凌叔华的作品不多,论影响力也不如林徽因、冰心等女性作家,但其作品的独特性,足以使她屹立于五四文坛。
夏志清在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中评价凌叔华说,“在创造的才能上,这些人都比不上凌叔华”,因为凌叔华“作为一个敏锐的观察者,观察在一个过渡时期中中国妇女的挫折与悲惨遭遇,她却是不亚于任何作家的”。

即使与她的丈夫陈西滢公开骂战的鲁迅,也中肯地评价道,“她恰和冯沅君的大胆、敢言不同,大抵很谨慎地,适可而止地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。即使间有出轨之作,那是为了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,终于也回复了她的古道了。这是好的——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、黎锦明、川岛、汪静之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,也就是世态的一角,高门巨族的精魂”。
要了解凌叔华,就不得不说一下鲁迅所讲的“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”创作出的“出轨之作”了。它正是1925年1月刊载于《现代评论》的短篇小说《酒后》。该小说的问世,让凌叔华一举成为闪耀文坛的新星,周作人、朱自清、沈从文等文坛大家纷纷投来肯定与赞许的目光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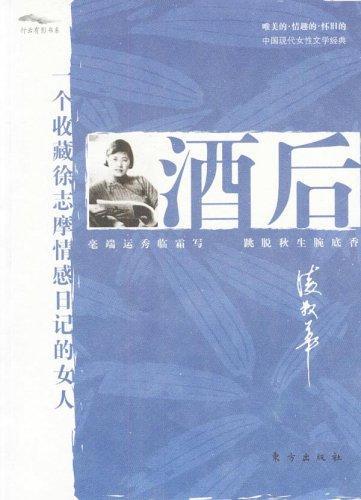
凌叔华同名短篇小说集,本文只就《酒后》一篇讨论
但和鲁迅一样,很多人将这篇小说定性为“出轨之作”——一个女人,有一个全身心爱自己的丈夫,竟还不知足,居然恩将仇报希望丈夫允许自己当着他的面亲吻一名醉酒的男子,虽然最后她“回复了她的古道”,没有亲吻那个男子,但也算是“精神出轨”。
即使在今天,也很少有人敢这样“明目张胆”地书写出轨。
但这真的只是一个单纯写出轨女人的作品吗?有人说,这篇小说实际上是凌叔华个人生活的写照。实则不仅如此。深究来看,《酒后》其实是一部“五四”时期的女性作家,使用最为大胆的方式,对压抑了数千年的女性这一群体的欲望与爱情伦理,进行的探讨与书写。
01.《酒后》中女性欲望的双重镜像
有文章评论《酒后》塑造了一个“理想丈夫的形象”,“勾画了男性与女性融洽相处的温馨情景”。这个结论实在是忽略了凌叔华女性写作视角的重要性。如果仔细分析小说中两人关系的描写,就会发现这对新式夫妻之间的温馨是多么的尴尬。
《酒后》中,凌叔华不露声色地展现了身为女性才有的情欲。她通过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,将采苕“浮现欲望—言说欲望—消弭欲望”这一流变过程进行了书写,呈现了女性欲望挣脱又受虐的双重镜像。
挣脱指的是:从道德上来讲,采苕和永璋是夫妻,他们通过自由恋爱而结合,理应尊敬与爱丈夫,不该再对别的男子产生爱情。
但采苕止不住地去看酣睡的子仪,“自从认识子仪就非常钦佩他;他的举止容仪,他的言谈笔墨,他的待人接物,都是时时使我倾心的”,而“愈看他,愈动了我深切的不可制止的怜惜情感,我才觉得不舒服,如果我不能表示出来”。
伦理的限制,让采苕不得不压抑自己对子仪的欲望,只有此刻的幻想,能让她暂时从道德的枷锁中挣脱出来。
但丈夫永璋的喋喋不休,却阻断了她欣赏子仪,令她大为恼火,“你却滔滔不绝,不觉得渴吗”?
无形中也进一步刺激了采苕的欲望。不能直言的爱,压抑着采苕,使她倍感受虐。
推动情节走向高潮的是丈夫永璋的一个“讨好”行为,他问采苕,“大后天便是新年,我可以孝敬你一点什么东西?”
永璋的发问给了采苕受虐延缓的时间,她试图从受虐中挣脱出来,无果后又在丈夫持续的讨好中,表达了自己的愿望。
“我什么也不要,我只要你答应我一样东西……只要一秒钟。”
“我只想闻一闻他(子仪)的脸,你许不许?”从后文来看,“闻”指的就是“吻”。
这里有意思的是采苕与永璋之间不断推拉的对话。提出诉求的采苕,不断向丈夫论证自己欲望的合理性;即使丈夫最终答应了自己的要求,采苕也希望他能“陪我走过去”, 这体现了女性自我欲望实现时的不自信——在两性关系中,永璋对采苕是“讨好”的。但一旦触及到伦理道德层面,永璋男性权威的一面便暴露出来。采苕的不自信,侧面也反映出男权社会对女性压抑的影响之深。
最终,采苕并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。作者写道,“我不要Kiss他了”。
这一举动,令采苕的受虐达到了高潮,从开始的想挣脱,到完全自由,再到她主动拒绝。她最终选择站在男权社会的立场,回归到社会对女性“守妇道”的认知中,从而消弭了自我欲望。
02.凌叔华对女性爱情伦理的个人化思考
《酒后》中,采苕的欲望看似是子仪,实则却是试探与挑战以丈夫永璋为代表的男性权威。那么,作者为什么要以婚姻为切口讨论女性欲望问题呢?
杨联芳在《性别视角下激进主义思潮与文学》一书中,论述了“恋爱”这个新名词是如何成了“五四”的关键词,又是如何对影响了当时的知识分子们的。
她说,东西方不同流派的爱情哲学与伦理观念撼动了封建保守的中式情爱,这些观念中“个性自由”思想正契合了“五四”时期的需求,因此,广受当时年轻人(尤其是知识分子)的欢迎。
《酒后》正是“五四”时期女性情爱意识觉醒和表达的作品,采苕在心理与情感上的蒙眬与清晰、挣扎与试探,充分体现了凌叔华对女性爱情伦理的个人化思考:“爱情”是一种个人情感的自由表达。
在凌叔华看来,表达对异性的欣赏与爱慕,是正常的情感流露,并不违背伦理。采苕清醒地知道她对子仪的欲望来源——一方面是他的外貌和言行吸引,另一方面,是对他不幸婚姻产生的怜惜之情。矛盾的感情令她无法理性思考自己对子仪到底是不是爱情。
驱使她将自己的想法大胆表达出来最根本的原因则是,丈夫永璋是一位新式知识分子,他充分了解、尊重妻子的情感,并允许、鼓励她按照自己的方式表达出来。
“很早以来,爱情就是人道主义、人人平等的思想的宣言书。”凌叔华的情爱观念可以看作是“五四”时期女性摆脱奴役、追求平等与自由的意志表达。
有人说,这篇小说完全是凌叔华自己的情感生活写照:丈夫陈西滢曾在北大任教,梁实秋称他为“五四以来五大散文家之一”,更重要的是他是凌叔华主动追求来的。
凌叔华与丈夫陈西滢
与采苕的克制相比,凌叔华本人的思想更加开放。与鲁迅骂战后,陈西滢被遣武汉大学执教。正是在这里,凌叔华认识了来自英国的朱利安(弗吉尼亚·伍尔夫的侄子),两人互相吸引,迅速陷入热恋,并大胆实现了采苕未能实现的愿望。得知这一消息后,陈西滢自然十分生气,他给了凌叔华三个选择:一,离婚。二,不离婚,分居。三,与贝尔断绝来往。处世精明的凌叔华选择了三。
英国青年朱利安
很显然,采苕身上有凌叔华自己的影子,但采苕又并非凌叔华意淫的产物。她用探索者与观察者的双重身份,审视着那个年代里女性世界的悲欢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,《酒后》是高于她的个人生活的。
03.凌叔华写作的独特性
凌叔华在“五四”时期的文人当中,无疑是奇葩般的存在,她的作品题材另类,叙事审美独特。即使在今天来看,也是十分前卫的。
笔者认为,造就凌叔华写作独特性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:一是她旧式高门巨族的生活;二是她接触到的新式知识分子。
民国初年,凌叔华出生于一个高门巨族(今北京史家胡同)。在这里,她目睹了旧式大家庭特有的妻妾成群、争宠夺利、重男轻女现象。凌叔华是庶出的女儿,但她从小显露出的写作、绘画天赋,让父亲对她偏爱有加。参与社交、留洋国外,父亲的默许让她发现了更多的自由和未来的可能性。
凌家宅院一角
凌叔华一家接待外国友人
纵观凌叔华的作品,她的主要写作对象正是“旧家庭中的婉顺女性”。这里的“旧家庭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封建家长大家庭,而是像凌家一样受到新思想洗礼的“旧家庭”。
“五四”时期,虽有部分女性觉醒,但社会的残酷让她们举步维艰——新思想与旧生活的反差,让女性在追求新思想的同时,又受制于传统礼教。由此可见,女性追求自身解放之路还很漫长。
凌叔华通过笔下的人物,诠释了她所认识的理想的女性意识。因此成为“新闺秀派”的代表。
另一方面,凌叔华接触到的新式知识分子,促使她逐渐产生了现代思想的萌芽。
凌叔华的“小姐的大书房”,举办过各种高端的文化沙龙活动,徐志摩、陈西滢、齐白石、陈师曾都是她的座上宾。在文学、作画的交流中中,凌叔华潜移默化接收了很多新思想。有人说,凌叔华之所以嫁给陈西滢,正是因为他曾留洋接受许多新思想。
此外,泰戈尔、伍尔夫也在凌叔华的交际名单之上。泰戈尔曾夸赞她,比林徽因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伍尔夫则指导她用英文写出了《古韵》这部自传小说。
凌叔华《古韵》
新月派作家们评价凌叔华是“中国的曼斯菲尔德”,这个说法其实并无贬义,而是说二人思想、创作以及活动轨迹的相似性。就创作而言,二人都聚焦女性日常生活小事,通过挖掘这些女性的生活、情感以及命运,表达出对这些女性的关怀,以及对她们所处环境和社会制度的不满和鞭笞。从这两位作家身上,我们看到了东西方女性作家思想的同步性。
《酒后》出版至今已经近一个世纪了,凌叔华作品中对女性意识的探索、理想和诠释,在今天仍有指导意义。当下,“干得好不如嫁得好”“女人最重要的是家庭”的观念依然有很多受众,这实在是与全球视野下女性追求平等、独立的潮流相矛盾的。
将幸福和快乐建立在自己身上,才能真正找到、把握住幸福和快乐,做到这点,才是女性意识真正的觉醒。